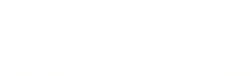4月23日晚18:30,通识讲堂之“一师一课一本书”系列讲座第八场《<道德经>的未来阐释与“新子学”》在钉钉平台准时开讲,由我校人文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陈成吒老师和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达老师共同主讲。讲座吸引了近两百人参加,其中还有一些感兴趣的校外研究人员。两位老师基于《道德经》向我们阐释了5个方面的内容:从《道德经》与疫情防治、全球化、未来世界,老子诞生与诸子百家的关系,《道德经》的撰写及其对历代思想家的影响,到经典阅读的创造性与“新子学”创构等等。通过将书中略有晦涩的哲学观点与现实以及未来相结合,用对谈的方式阐述探讨同一个话题,从多种角度分析,极大地开拓了听众们的视野。

讲座伊始,陈成吒老师以“《道德经》对于疫情防治,世界发展和逆全球化等问题的一些启示”开始了与方达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陈成吒老师引用了《道德经》第六十章的内容阐释了治理大国家,要采用亲近无为的道的方式,不仅对百姓受益,而且可以防治鬼怪(此处可指灾害)。对于当下的道可具体指基层较强的能动性和政府的权威且不可过度干预,强调了道对治国重要性。方达老师以鬼神和圣人为切入点,展开其历史,谈论到了个人自由的权限。方老师认为基层自治是应该的,但对其效力抱有怀疑。



在题引之后,二位老师对全球化也开展了讨论。方老师将全球化细分为两个部分: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探讨了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以及背后原因,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更大。但陈老师则认为经济层面占的更多一点,引用了《道德经》第六十一章的内容,指出越是大国要更加谦逊低调取得小国的认同和信任;低调,让利对于国家间相处是关键。但同样是六十一章的内容,方老师却读出来去全球化的味道,不能一以贯之固定的认为大国就是大国,小国就是小国,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变化。



紧接着的书籍导读部分,陈老师对老子和《道德经》做了简要的介绍,并向同学们推荐《史记》中的《老子韩非列传》。


荀子是第一位指名批评老子的,方老师阐释到:荀子认为老子过于向内发展,保守,不太重视外在治理。陈老师则通过历史上朱熹,韩非子等对老子的批评表达了老师对于不同声音的尊重和重视。


陈老师表示经典阅读的创造性与新子学的创构是紧密关联的,希望同学们自己去参阅方勇教授和两位老师所撰写的相关论文。方老师表明,新子学实际是对当下传统经典的再吸收再看待,此中有两个问题:如何正确看待经典文献本身的含义;如何与当下诉求进行对接。

老子的“道”和加缪的“荒谬”是否有关联及其区别?老子的“自然”可以让其心情平静,但随之会有“不求上进”的想法。加缪说的“荒谬”对其也有类似作用,但加缪同时强调在走向结果虚无的过程中,人要去做事,要用行动去抵抗。我感觉《道德经》和加缪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为补充,但说不清其中的关联。
我对于加缪不十分熟悉,但就刚才同学所说的来看,两者有一定相似性,但也有很多区别。如老子的“道”“自然”及其“清静”“无为”等,的确有“我本自然”“本性清静”等这一层面的内涵,但它又是立足现实而言的,现实是一个由观念塑形的世界,人一生下来就沉溺其中,不断受其染著和搅扰,所以现实中的人多是处于沉沦状态,因此要做的是“损之又损”与“为无为”,就是努力克服身上的陈见与观念搅扰,走向清静,是以“为”走向“无为”;至于加缪的看法,虽有相似之处,但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倾向,而老子对于现实是满怀热情的,否则不会写出极具批判力的五千言。
在我眼中,老子与加缪之间的区别太大,之前也没有想过把他们拿来比较,毕竟他们的思想背景完全不同。
的确一些看似很相近的词语,甚至是同一个词语,如果是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它们的内涵也是截然不同的。
儒家的是有烟火气的人间圣人,道家是宇宙中洞悉一切又遥不可及的圣人,治国的优劣上看,完全采取道家在现阶段肯定无法达到,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半道家、一半儒家?
儒道融合,是可行的。我认为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甚至你可能会想到“百家融合”,我也认同你的想法。